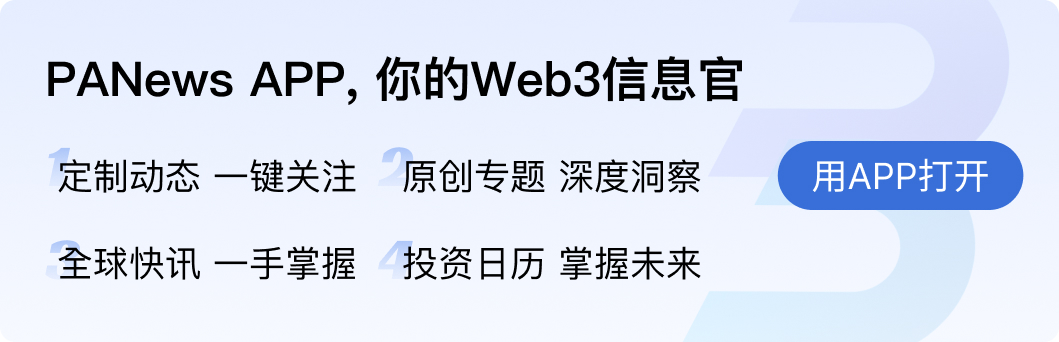将时间拨回到五万年前,彼时人类还处于旧石器时代,但茹毛饮血已经是过去式,我们的祖先对于工具的使用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工制品的多样性显著增加,每个工具都会为一个特定的目的而打造,史上首个艺术品在非洲诞生,新工艺随着人类的脚步来到亚欧大陆,文明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我们物种浩瀚的历史已经走上正轨,但远在南半球的一个小岛,塔斯马尼亚岛,却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事。
随着全球温度不断下降,最后一个冰河期来临,大量的海水被锁在冰川之中,海平面远比现在更高,早期人类也借此进一步扩张版图,一步一步走到了塔斯马尼亚地区。后来冰河期结束,海平面上涨,塔斯马尼亚岛与澳大利亚大陆见形成了当时的人类无法逾越鸿沟,巴斯海峡,塔斯马尼亚的原住民自此再也无法与外界人类来往,而现实中与世隔绝的生活并不像《桃花源记》描绘得那样美好。

刚开始,塔斯马尼亚人也拥有先进的狩猎技术,或许也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景象,但丰富的自然资源让他们对于技术的发展再无动力,曾经掌握的技术变成了长者脑中的回忆,曾经使用的工具渐渐磨损殆尽,捕鱼、狩猎、骨器、衣物,都慢慢消失。在与世界中断联系一万年后,塔斯马尼亚人的文明回退到了十万年前。生物学角度来说,他们与现代人类无异,但在孤立的环境中,资源无法被补充,信息无法被迭代,社会规模再也无法承载文明的传承,终将走向消亡。如同前篇所讲,交流是我们认识自我的渠道,也是进步的源动力,室外并非桃园,封闭只会是文明的灾难。
在当代的信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无限缩小,狭义的塔斯马尼亚效应很难再次出现,但这一警示依然足够有意义。
从小尺度来说,无论是被动承受的信息平台分发,还是主动选择的社交网络,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壁垒越来越高,即便大家使用相同的语言,一个群体的人完全无法理解另一个群体的人的想法,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封闭内部的信息交流很少会产生矛盾,这种“舒适区”当然会很安逸,但随着更大群体的不断进步,长期停留在自己的认知当中,拒绝与外界沟通,这本身就是一种思维上的相对退化,社会意义上的废人在今天并不罕见。但现在这个时代的信息获取成本极低,封闭多数时候只是个人选择,海量的知识不会拒绝任何人,陷入孤岛的个体终究是少数人,但当代的塔斯马尼亚效应不止如此。

从大尺度来说,人类社会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封闭体系,地球空间并不是无限的,有限资源会被消耗,无限能源还遥遥无期,即便信息量极大丰富,也仅仅是人类内部的产物,如果没有与外部的交流,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我们是不是像玛雅文明一样,没有点亮某项科技或采取了某项错误的策略,而走在了灭亡的路上。我们把太多精力放在了人类内部创造的事物当中,但正如热力学第二定律所陈述的一样,没有外部输入,孤立系统只会逐渐熵增,目前我们的文明仍在进步,是因为这个系统足够大,未被开发的部分还有很多,但这并不能让我们消除警惕。
星辰大海是向系统外部的探索,而元宇宙便是从系统内部开拓出一个更低维度的世界进行探索,而即便在有限的高维世界中,低维物体的量也是无限的,这一部分我们将会在之后有关维度的部分探讨。元宇宙首先是一个向内探索的交流媒介,未来也有机会发展成一个虚拟社会,甚至是原生的虚拟文明。
在前篇文章中,我们将媒介分成了记录型媒介和传输型的媒介,前者扩展了信息传播的时间,使信息得以延续到后代,后者扩展了信息传播的空间,使信息得以播撒到更多的群体当中。如果说黑格尔从逻辑出发,推出了一个脱离具体事件的历史模式,那么伊尼斯则从媒介的时间与空间偏向的角度,根据信息时代的景深,在经验中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历史是一出戏剧,整个世界就是剧组,本篇文章将从媒介的角度,将人类文明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逐一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并进一步探讨元宇宙对于我们的实际意义和影响。
回顾过去的文明
1. 埃及与苏美尔
人类文明滥觞于河畔,而最早的可以被称作文明的聚居地来自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尽管两者都早已消逝,但还是可以从对古迹的解读中对文明的发展脉络窥得一二。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在古埃及,尼罗河每年都会泛滥,淹没农田,但随之带来的是肥沃的耕地。因此尼罗河的不规则泛滥成为部落居民们最大的困扰,也是缔结成社会组织的主要因素,当合作成为必需,只有被普遍认同的共识,才能让人们消除芥蒂,团结起来从事集体工作。早期的埃及人发现,通过天文观测,可以准确地预测尼罗河泛滥的时间,因此从天体中抽象出来的神明成为了他们最核心的共识,历法成为了统治者权威的根源。埃及的最高神被叫作 Ra,是太阳的化身,创造了一切人界和神界的秩序。

君权神授的背景下,第一王朝即提尼斯王朝的开国之君美尼斯提出了绝对王权的理论,王朝开始集中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成为人们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是基于对神祇的崇拜的,法老便是神明的代言人甚至是神明本身,敕令相当于神明的指示,在这种统治结构的基础上,法老权力则逐渐演变成了宗教信仰,权力也逐渐分散到了神职人员的阶级。这种基于宗教的统治给埃及文明带来了很大的发展压力,技术变革和军事力量难以发展,公元前十七世纪,闪米特人带着长剑和强弓击溃了埃及并建立起牧羊王朝。
尽管容易被击败,但基于宗教的国家,文化才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文化的复杂性让埃及很快东山再起,建立起新的底比斯王国,第十八王朝,在阿梅诺菲思三世的统治下,埃及帝国达到了国力的巅峰,但宗教弊端再次显现。推行帝制或者王道是超越狭隘的民族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中央集权是第十八王朝得以强盛的根本原因,但宗教信仰才是维系埃及文化的内核,而宗教领袖却无法容忍异教徒,早在三千年前,国际化的趋势便被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裹挟,这与今天的逆全球化如出一辙。宗教领袖和法老贵族代表了彼时的右派和左派,随着图坦卡蒙恢复了传统的宗教统治,在第十九王朝,宗教阵营完全得势,神权统治彻底代替了人权统治。一时的繁荣却无法解决宗教国家的根本弊端,埃及王朝逐渐走向衰落,在后来在面对亚述、希腊和波斯人的入侵时,埃及文明也渐渐消亡。
古埃及文明蔓延 3000年,历经 31 个王朝,统一王朝的产生是文字发明的基础。最初,文字是神圣的,是神向人间传递信息的媒介,文字和图像被记录在石头上,用来记录大型战争或政治事件,但更重要的是阐释宗教教义,描绘神祇形象。永恒不衰的文字是神职人员们垄断权力的法门,象形文字书写极其困难,不仅需要长期的学习过程,还需要特殊的篆刻技艺,知识的传播权和教义的解读权都集中在了某些特权阶级手中,长此以往知识形成了垄断,这也是宗教领袖权势极大的基础。

同时法老修建金字塔以加强自己的地位,石制的建筑和雕塑也反映了法老作为统治者的权力。当埃及试图实现帝制,扩展自己的疆土时,石头的不便以及文字的复杂的缺点变凸现出来,这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时作为传输型媒介的莎草纸出现了,可以突破物理媒介的限制,将信息传播给更多人。莎草纸最早出现于埃及的第五王朝,随着王权和神权的融合,在第十八王朝这种媒介成为了埃及繁荣的助力,但根深蒂固的神权思想,使文字的主要目的依旧是处于宗教意义的,知识的垄断并没有得到破解,普通人依旧无法解读复杂的文字信息,而行政对于文字的依赖需要得到宗教组织的庇佑,因此莎草纸更多地成为了宗教传播的媒介,而非更具普世价值的知识。
在埃及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神权政治始终都压制着王权政治,短暂的融合缔造了最强盛的古代帝国,第十八王朝,但并不长久。石制媒介可以长久保存,作为记录型媒介成为了王权统治的基础,而文字本有机会解决空间扩展的问题,却因为极其复杂的书写和强烈的宗教属性,莎草纸这种传输型的媒介非但没有扩大王权政治,反而成了传播宗教的工具。伊尼斯在解读媒介时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意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命问题,也是宗教问题。文明发展莫不如是,埃及文明本拥有解决空间问题的手段,却还是倒在了时间问题上。
但莎草纸作为一种解决空间问题的传输型媒介并非没有意义,在美索不达美亚平原的文明发展过程中,正是莎草纸的发展给巴比伦帝国带来了长久的平衡。

在两河流域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经过改造以适应灌溉,苏美尔人没有对于汛期的顾虑,这也促成了苏美尔早期的文明形态是以城邦制为主的,比较大的城市有基什、拉格什、乌鲁克等等,但和埃及类似的是,这些城邦的统治同样是依托于宗教的,祭祀作为宗教领袖是城邦之神,而君主虽然拥有处理民事事务的权力,但只是神的仆人而已。
不同于纯宗教性质的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地区不同城邦之间会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因此文字的诞生更多是出于世俗意义的目的,比如记录账目、买卖契约、编纂史书等等,而文字选择的媒介载体则更代表了苏美尔的文明特色。冲击平原带来了大量黏土,这种优秀的材料不仅可以搭建建筑,还可以烧制成泥版用来书写。早期文字当然都是从图画演变而来的,但是在泥版上刻字需要更合适的工具,芦管笔应运而生,这种笔尖呈三角形,书写时需要垂直用力,这使得书写时要尽量减少刻画的次数,因此象形文字逐渐没落,楔形文字粉墨登场,文字从图形向着符号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表现更多的词汇意义,表音符号也就出现了。
宗教性质的泥版适宜长期保存,但不利于远距离传播和大规模管理,而楔形文字却有利于文字的规范,宗教使用文字的特权被打破,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交流成为了可能,这种微妙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众多小城邦早期可以各自独立存在的原因。但随着财富和资源的累积,这种平衡注定无法维持,于是城邦之间的战争接踵而至。公元前 2334 年,闪米特族的阿卡德城邦统一了美索不达美亚区域,并建立了君主制的集权国家,结束了七百余年的城邦时代,这也为后续的乌尔第三王朝和巴比伦帝国树立了标准。

闪米特人再次加速了文字发展的进程,与苏美尔文本的接触,使他们意识到了抽象符号的巨大意义,于是他们采纳了楔形文字的符号,但放弃了苏美尔的语言,而是将自己的阿卡德语移植到了楔形文字中。这使得苏美尔语成为了死的语言,但却带来了人类最早的字母表,闪米特人在公元前 1500年与埃及人接触并发明了字母表,由巴勒斯坦人加工,腓尼基人完善。莎草纸终于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与字母表的结合之后,信息得以迅速传播,因此简单的文字成为了众望所归,这彻底摧毁了宗教体系下的知识垄断,为帝国的统一政治组织奠定了基础。
灵活的字母表为后续腓尼基语、希伯来语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这也促成了整个印欧语系的发展。这种新的媒介诞生之后,帝国的统一管理成为了可能,空间问题得以解决,而新型文字同样可以服务于宗教,第一,为了方便政治管理,一神教成为了主流,规范的宗教可以进一步强化统治,第二,宗教与秩序的碰撞中,法律逐渐成长起来,最早的《乌尔纳姆法典》以及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都是宗教的一种弹性化表现,一神教和法典解决了时间上的问题。从巴比伦、赫梯,到亚述、波斯,尽管朝代更替,但是中央集权的体制一直持续了下去。
2. 希腊与罗马
你发明的文字使习字人的心灵患上健忘症,因为他们不再使用自己的记忆;他们会相信外在的文字,记不得自己、你发明的这个特别有效的东西不能帮助记忆,只能是帮助回忆。你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他们能记住许多东西,但是学不到任何东西;表面上他们似乎什么都懂,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伙伴,有智慧的显露,无实际的货色。
这是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专属埃及透特神谕阿蒙神之间的对话,正如前篇所说,文字是冰冷的,并不会给予提问者任何动态的回复,对于任何问题的回应都是一成不变的。文字会扼杀掉信息中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古希腊人在文字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另一种传播媒介——口头传播,在接受了闪米特的字母表的同时,将其修正,以适应自己丰富的口头传统的需要,并将其发扬光大。

口头传播的媒介形式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延伸也都有与文字截然不同的影响。
口头传播隐含着一种适合其自身所在场合所需形态的创造力,可以灵活地使用语言的不同表达方式来呈现出与文本截然不同的信息。口头传播和字母表的使用,使宗教体系带来的知识垄断没有在古希腊发生,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歌的宗旨和宗教基本相同,同样是对于文化价值的传播,也同样依赖于时间,只不过记录方式从石刻泥版变成了口耳相传,这也是希腊没有形成大规模宗教系统的原因之一。
从早期的短小叙事诗,到后来宏大的史诗,再到抒情诗,便是口头传播的集大成者。以《荷马史诗》为代表,荷马家族从古老文明中吸纳神话,再进行个性化的加工,使之成为英雄神话。神祇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被拟人化为具备人格的英雄。当神不再是统治者的化身,而成为了某种普适的精神的传扬载体时,寻找世界的真理便有了必要。这让希腊有了理性和逻辑诞生的土壤,当没有了所谓的神圣文字时,科学和数学出现了,并在其自有的体系结构中自由发展,理性主义成为了大众的信仰,引领了古希腊文化的空前繁荣,宗教的地位被自然规律所替代。

口头传播对于空间问题的影响则更加明显。正义和公平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适价值观,当宗教地位式微,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便会由公民来控制,个人拥有一定的立法权,司法制度也允许人们伸冤,国家规则可以不断灵活地调整,贵族不再凌驾于人民,普通公民拥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雅典的统一法典发展缓慢,但可以最大程度上地使个人不受拘束地发展,这也是民主的雏形。
这种口头传播的方式在国家管理的空间扩张方面并不有利,个性化的民主会加剧城邦之间的鸿沟,大规模管理难度很大,远逊色于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度,而对于控制人民行为方面自然也不如神权统治,但却提供了一种更美好的社会形态。希腊人把时间和空间压缩到了城邦这种合适的比例,为现代社会指清了方向。
与古希腊对于口头传播的坚守不同,古罗马则将书面文字贯彻到底,为现代文明提供了另一个必备的要素——契约。
在西塞罗时代之前,法律受口头传播影响很大,法律的解释权都归于人,而这些规则过于弹性,尽管执法平等,却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人们使用契约来取代不成文的权利与义务,用来保护个人的财产和利益。在国家层面,罗马不在满足于城邦的狭小区域,以武力开辟疆土,而共和制却面临着难以管理的问题,治理辽阔的疆土必须倚重官僚行政,元老院可以管理国家,但是无法统治国家,因此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帝制则开始兴起,随着行政权力的增加,王权愈发集中起来,固定的法律可以省去很多精力,因此作为固定文献的法典在罗马帝国成为了统治者的工具。法律文本至高无上,不可修改。古代罗马法学家的成就,是历史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证据,足以说明,物质的不灭与思想之不可摧毁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罗马帝国的行政权力扩大与莎草纸的通行有极大关联,由于幅员广阔,倚重空间的媒介对于中央集权的管理体系帮助很大,但政治统一的过程却忽略了个人的宗教需求,严格的规定取代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学者们加强了基督教的地位,一世纪默契,罗马教会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有赖于羊皮纸的流行。羊皮纸抄本适合长期记录和检阅,自然成为宗教与法律经典的书写材料。由于图书馆制度的建立,羊皮纸抄本的盛行获得了制度与版本的双重保证。《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会手中,对教义的垄断通过修道制度进一步扩大,也引发了教会权力的扩大:世间一切生灵,若欲获救,必然臣服罗马教皇,诚乃万万之须也。
莎草纸有利于帝制的发展,扩展了空间,羊皮纸有利于神权的发展,延续了时间,在希腊式的民主之外,罗马帝国通过皇帝和教会的双重统治找到了一种集权高压但能量极强的形态,这也构成了人类史最长久稳定的帝国之一,拜占庭帝国,即便在现代已经显得不具人性,但仍然存在于很多国家当中。
3. 启蒙运动

从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的几个典型实例来看,文明的政体无外乎帝制和共和,而当社会走向正轨,文化与精神便成为了维系社会的信仰,宗教和科学是最常见的选择,前者完全垄断了知识,后者消解了这种垄断。文明衰落并不罕见,转化也经常发生,扩展空间的传输型媒介会影响政体的选择,而扩展时间的记录型媒介会影响信仰的选择,后世的传播媒介都是对这二者的强化。
启蒙运动,是人类科学发展最美好的时代,也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受科学发展的影响,人们试图重回古希腊的模式,认为普世价值可以建立在科学及理性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更满足公民个性的社会制度才是大势所趋。科学在古希腊兴盛史口头传统最后的荣光,然而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时代,帝制控制着人民的行为,基督教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宗教哲学将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视作启发宗教精神和揭示基督教真理的工具,而这种根深蒂固的统治思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文主义的复苏,被逐渐动摇。
从媒介的角度来说,思想的扩展便是来自于纸张的普及和印刷术的发展。一方面普通人可以获取到更多知识,法国在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出版物——《百科全书》体现出现代理性思维的雏形,以包含所有人类知识的名义来宣扬科学实证精神,虽历经法国政府屡次打压,仍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而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则通过艺术来证明个体的个性化以及创造力,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都是对于长久以来被压迫的思想的重塑;另一方面,机器印刷《圣经》大幅降低了《圣经》的价格,普通人接触《圣经》的机会大大增多,教会通过解读圣经以实现知识垄断的操作逐渐作古,印刷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欧洲大教堂不占据支配地位的地区,是政治分裂最令人瞩目的地区——意大利和德国,这同样也是艺术和哲学成果最多的地方。

印刷媒介的非集中化特性,却加大了地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不均衡,最终导致现代基于民族的国家组织的出现。积极的角度来看,印刷术的普及,瓦解了教会的知识垄断,使科学知识和独立精神的普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从消极的角度,正是这场技术革命塑造了新的知识垄断,以机器为生产资料,以金钱为扩展手段的新形态帝国形成了,技术和资本成为了新时代的垄断工具,直到今天仍然在侵蚀着我们的文明。
4. 工业革命
如果说启蒙运动重塑了记录型媒介的话,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工业革命则大大拓宽了传播型媒介的边界,空间的偏向空前提高,世界完成了万年来最大的变化,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们介绍了电的诞生,发电机和电动机让能源结构完成升级,技术革命是社会生产了完成了从手工劳动向着动力机器的重大飞跃。机械化对印刷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寿命短暂的东西日益重要,信息量在极大丰富的同时,可以快速触及到所有人,从报纸到无线电再到互联网,体量越来越大,延迟越来越低。知识垄断不再是对于只是本身的垄断,而变成了对于分发方式的垄断,当知识量极少的时候,知识依靠复杂的文字或者独享的解读方式,成为少数人才能拥有的存在,从而形成垄断,而当知识量极大的时候,对于知识的快速获取和筛选将耗费大量资源,普通人无力承受,而这种分发渠道形成了垄断。
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肤浅的内容势必成为流行,甚至被变成艺术,而深度的内容反而会成为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新闻产量的剧增,报纸篇幅的增加,各种低级的营销手段,大量的广告,煽情的故事以及虚假信息的传播,终于在普利策与赫斯特的战斗中达到顶峰。大字号煽动性标题,对小事件的加以渲染、夸张,捏造访谈记录和新闻报道,引起歧义的标题,大量未经授权或真实性可疑的图片,肤浅的内容,煽动社会运动,妖魔化某特定群体,这是十九世纪对于黄色新闻的评价,直到今天仍然适用。

现代文明更在意空间上的影响,却缺乏对时间延续性的关注。《摩登时代》中演绎的标准化、无个性的生活即景每天都在上演。口语和手稿的传统开始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媒介所取代。世界在聒噪的大众媒介中成为“一天的世界”,对时间的压缩也是进一步印刷媒介的空间偏向,现代文明成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
本文版权所属 ArtGee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