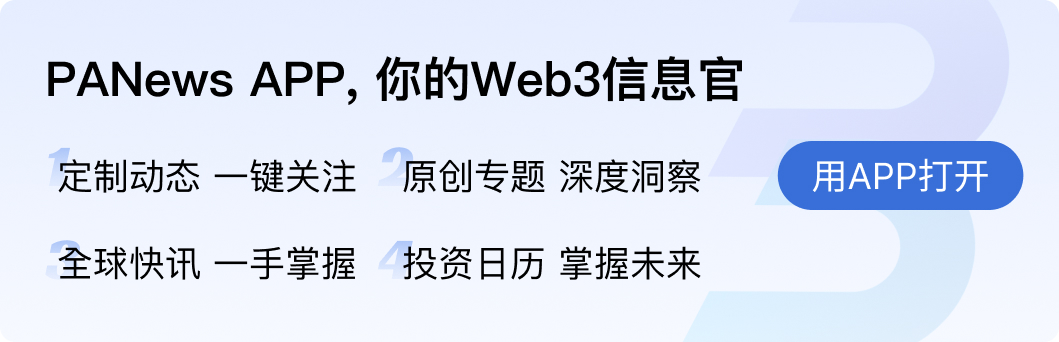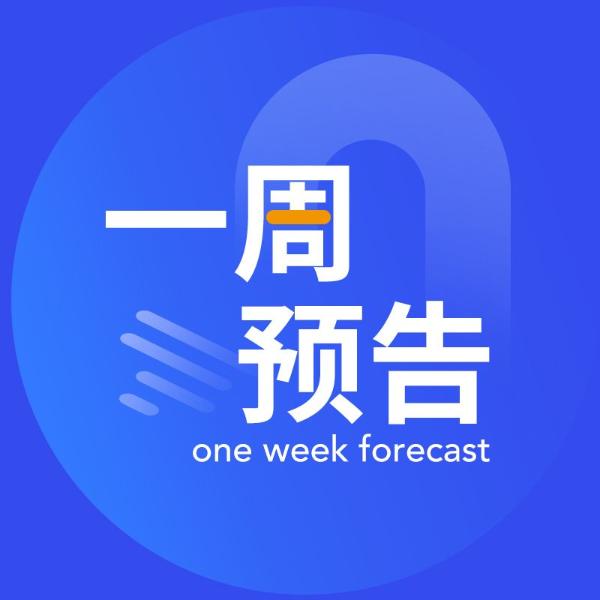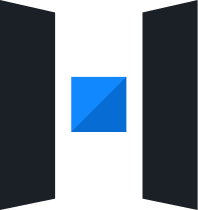作者:幣安創始人,趙長鵬
文章來源: 幣安博客
我們在幣安的員工必須具備的眾多優勢之一就是厚臉皮。畢竟,這個行業是很多負面情緒的主題(其中大部分是沒有根據的,但這是現在的現實)。最近幾個月,我們厚臉皮受到了對我們公司聲譽的攻擊明顯增加的考驗。這些來自媒體和與政策制定者的閉門會議。
就在上週,一位前《華盛頓郵報》記者在Twitter 上就“媒體偏見”發生普遍分歧時向我們的一位高管發送了一條推文。他們出其不意地問道:“陳光英是誰?”
雖然那位記者可能不明白,但這個問題象徵著我們的員工在東西方每天都面臨著蔑視。這個問題源於競爭對手通過匿名小網站發起的一項舊活動。目標是在我們不斷擴張和競爭以吸引新的合作夥伴和投資者時,削弱對我們品牌的信任。
如果您查看我們的公司和FTX、Crypto.com 等公司,您會發現我們的組織擁有非常相似的員工資料。然而,在過去的兩年裡,隨著我們向歐洲和中東地區擴張並招募了更高級的領導團隊,Binance 的執行團隊現在更多地由歐美人主導。我們更廣泛的員工群分佈在全球範圍內。儘管有這些事實,但有些人堅持稱我們為“中國公司”,這樣做並不好。
這些類型的負面活動比人們意識到的要普遍得多。我們甚至看到加密貨幣交易所和項目創建了自己的“新聞”網站來抨擊競爭對手,而這些網站現在經常被谷歌新聞錯誤地歸類為獨立新聞來源。如果不是那麼嚴肅和令人沮喪的話,我不得不向真正掌權的人解釋像CoinGeek和CoinDesk 這樣的組織之間的差異。
而這些類型的攻擊只會變得越來越複雜。就在最近,CryptoLeaks 發布了一份報告,指控一家公司如何利用訴訟來質疑競爭對手的區塊鏈項目。雖然對從事這些活動的行業不良行為者發起反擊很誘人,但我們不會貶低自己,也不會放棄我們的價值觀。
這些類型的活動侵蝕了整個行業的信任。我們是建設者。我們可以在這個領域競爭,並且仍然為彼此的成功歡呼。
我們的職責
我們是地球上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和Web3 公司。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責任和麵臨額外審查的期望。但是,重要的是要記住,我們的行業仍處於起步階段。
當您的公司在一夜之間突然從初創企業躍升為財富100 強企業時,並不會在第二天擁有 1,000 名經驗豐富的高管、簡化的流程和技術,突然間像一家擁有200年曆史的老牌金融機構一樣運作。
與其他所有加密貨幣交易所一樣,培養和提升我們的員工規模以及使我們的系統成熟以適應行業的發展一直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大的挑戰。到目前為止,這是我接受並投入巨資的東西。
亞洲加密貨幣行業開花結果
在回到我的主要觀點之前,讓我提供一個快速的、過於簡單的加密行業歷史,令人驚訝的是,很少有人理解。在2015 年或2016 年左右的某個時候,該行業在韓國和日本的千禧一代中見證了第一波大規模的加密熱潮。
當時,兩個社會都對年輕男性越來越多地參與一種主要存在於網上的文化感到恐慌。這體現在這樣一種觀念上,即年輕男女只會在網上浪費生命,整整一代人都會消失。
所以你只能想像加密貨幣的興起是如何影響這些問題的。結果是韓國和日本發生了一系列加密貨幣鎮壓。在此期間,中國很快意識到擁抱這個新興行業有可能為其經濟帶來可觀的收益。
儘管中國政府在加密貨幣方面保持著嚴厲的公開立場,但它在幕後默默地幫助支持了新興行業並支持其在境內的發展。最優秀的對Web3 感興趣的工程師和投資者紛紛湧向上海和香港。
與中國的複雜歷史
1989年8月6日,我和母親離開中國,移居千里之外的加拿大。
我當時12 歲。
我的父母是老師/教授。我們當時住在合肥中國科技大學的校園裡,這是中國排名前四的大學之一。
通常需要四年時間才能拿到護照,如果幸運的話,還要再花2-3年才能拿到加拿大簽證。但由於這件事,加拿大大使館開門見山,很快就給了我們簽證。我記得加拿大大使館外的隊伍排了三天。我們不得不在晚上輪班以保持我們在隊列中的位置。
它永遠改變了我的生活,為我打開了無限的可能性。
我在溫哥華度過了青少年時期最好的時光,然後去了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上大學。之後,我在東京和紐約(彭博社)工作了幾年。
2005年,網絡科技行業開始在中國爆發,所以我和其他五位外籍人士一起去上海創辦了一家IT初創公司;兩個美國人,兩個英國人,一個日本人,還有我,一個加拿大人。該公司被指定為“外商獨資企業”(WOFE),因為我們都不是中國公民。
這一點是一個需要克服的相當大的商業障礙。當我經濟穩定到可以在上海購買公寓時,由於我是外國人,我不得不多繳25% 的稅。是的,我在2014 年為了購買比特幣而賣掉的同一套公寓。如果沒有這筆費用,我今天可以多擁有25% 的比特幣。
在2005 年到2015 年間,我嘗試建立幾個不同的初創項目,然後最終涉足加密領域。在我了解自己的熱情之前,我是一名連續創業者,希望建立一家成功的初創公司。
對於任何年輕的企業家來說,這是迄今為止最根本的挑戰。
在幣安的兩年前,我創辦了一家名為比捷科技的公司,為其他交易所提供交易所即服務平台。我們有30 個客戶加入,生意很好。它們主要是藝術品和郵幣卡等物品的交易。
不幸的是,2017 年3 月,中國政府關閉了所有此類交易所。我們所有的客戶都倒閉了。後來,幣安的想法開始形成。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即更簡化的加密交換可以在不犧牲有用功能的情況下提供更順暢的用戶體驗。
離開中國
我從比捷團隊中帶了不少人來到幣安,我們一起在2017 年7 月14 日推出了幣安。
然而,僅僅一個半月後,在Binance 還沒有建立起來之前,我們就面臨了第一次重大中斷。
2017 年9 月4 日,中國政府指出不允許加密貨幣交易所在中國運營。
然後他們在防火牆後面封鎖了我們的平台。此時,我們的大部分員工都離開了中國。到2018 年底,只剩下少數客戶服務代理。
我們的領導團隊共同決定我們將遠程工作。很快,COVID-19 傳播到全球,整個世界都轉向遠程工作。這使我們能夠繼續成長為一家公司並吸引頂尖人才,儘管我們仍在尋找紮根的地方。
Coinbase 甚至在納斯達克上市,但其S-1 註冊聲明中沒有指定總部。
此後,我們的遠程工作模式已在全球範圍內常態化,我們積極追求頂尖人才,無論他們來自哪裡。正如我所提到的,當我們五年前創辦Binance 時,我們是一群雜亂無章的加密愛好者和工程師。我們還必須應對在韓國和日本的鎮壓引發的熊市高峰期開展業務的挑戰。
從好的方面來說,這是進入加密貨幣的相對好時機,因為價格很低。這就是為什麼這段時間在香港設立了許多主要交易所,例如FTX 和Crypto.com。
“陳光英是誰?”
那麼在這樣的背景下,陳光英是誰呢?
2010 年,我第一次認識陳光英(Heina),當時她在我朋友的酒舖工作。她後來在一家大型商業銀行擔任服務經理,同時負責管理後台(人力資源/財務/行政)。
2015年,我創辦必捷科技的時候,我讓光英為我工作。我們讓她管理後台,因為早期的團隊主要是工程師。由於中國對外國人(如我,加拿大公民)的限制性法律,讓中國公民作為列出的法定代表人要容易得多。
鑑於光英既是中國人,又為我們管理後台,她同意了。這在中國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由於她的名字被列在了比捷科技的早期文件中,幣安的詆毀者趁機散佈了一個陰謀論,即光英是比捷科技的秘密所有者,甚至可能是幣安的所有者。
結果,她和她的家人都成為了媒體和網絡巨魔的目標和騷擾。如果我知道這會對她的生活產生多大的負面影響,我永遠不會要求她做當時看起來如此無害的一步。
與許多早期的幣安員工一樣,光英在2017 年我們大多數人離開中國時不得不離開她的家人、她的家和她的朋友。這是一個巨大的犧牲,她是為數不多的能夠真正理解其影響的人之一這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影響。今天,隨著虛假的中國媒體繼續散佈關於她的陰謀論,她仍然背負著這個負擔。
如今,光英是一個歐洲國家的護照持有者,她與家人過著相對平靜的生活。我說“相對和平”是因為小報經常挖掘這些古老的陰謀論,引發對她和她所愛的人的另一輪騷擾。
隨著我們過去五年的發展,許多原來的員工和創始人在組織中擔任了新的角色。光英目前負責該組織的管理和清算團隊。
所以總而言之,她不擁有幣安,也不是中國政府的秘密代理人。
那麼幣安是一家中國公司嗎?
不,任何對公司法或公司運作方式有初步了解的人都會明白這一點:幣安從未在中國註冊成立。我們在文化上也不像中國公司那樣運作。我們在許多國家設有子公司,包括法國、西班牙、意大利、阿聯酋和巴林(僅舉幾例)。但我們在中國沒有任何法人實體,我們也沒有計劃。我認為,今天我們提出這些事實至關重要。
幣安今天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我們(以及所有其他離岸交易所)在中國被指定為犯罪實體。與此同時,我們在西方的反對派卻把我們描繪成一家“中國公司”。
推論是因為我們有華裔僱員,也許因為我是華裔,所以我們秘密地落入了中國政府的腰包。我們很容易成為仇恨我們行業的特殊利益集團、媒體甚至政策制定者的目標。
這顯然不是真的。
我最喜歡的是那些特意強調我是“華裔加拿大首席執行官”或者更好的是“出生在中國,在加拿大接受教育的新聞報導”。我是加拿大公民。